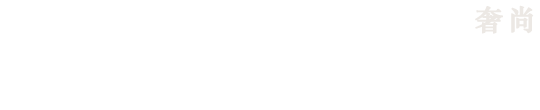[摘要]东方镜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更不是精致华美东方元素的代名词,那样的东方镜像过于单薄。传统是东方镜像的基点,存在于东方数千年的传统自有其随时间生长的生命力,自有其永恒之处,这也正是东方镜像生长的力量。除此之外,东方镜像自有自己融构异文化,并生发出新的自我的能力,自有以千年文化做积淀形成自我镜语的能力,并以此更好地表现自我,成长自我。最终,生长与强大起来的独立镜语体系,自会拥有吸引电影受众的魅力。
[关键词]东方文化;东方镜像;生长
提起东方文化,人们总是无意识地将其与老旧相勾连。的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东方文化多半属于保守老派概念。其原因就在于东方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发生质的蜕变,也没有跟随时间延绵到现今。而西方文化却一直在生长,在东方文化滞后之时,它反而成长得最为茁壮,电影艺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来到东方的。它带着西方文化写实的特性来到东方,工业落后的东方没有与它相对应的东方艺术,就像西方有歌剧,中国有戏曲,日本有能剧;西方有油画,中国有水墨画。随后,电影艺术跟着西方持续发展的文艺思潮与高度发达的工业一步步生长蜕变。而东方的电影艺术却没有如此优越的环境供其成长。“历史的变化,让东方陷入了失去自我诠释能力的尴尬之中,自我意识的迷失,甚至使东方丢弃了在整个世界大舞台中应有的形态。”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东方电影一直生长在西方电影的阴影之下,当然也包括现在,无法展现出自身独特的魅力。所以说,东方电影需要自己的生长蜕变,才能将精良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在银幕之上。总的来说,东方电影的生长,一是需要让传统随时代生长,保留住传统中的永恒美。二是以自身文化为中心,并以自身文化弥补异文化缺陷,然后再将异文化融构进自身文化,以提升自身文化。三是独立东方镜语体系的建立与受众培养。
一、永恒的传统美:古代-现代-未来的传统美
东方镜语的成长力量之一正是东方传统。它的成长需要外来的内容,但更需要供其生长的土壤发挥效力。不同的土壤培育出不同的电影,所以东方电影的生长力量最终要到培育它的土壤里去寻找,何况电影是土腥气比较重一种艺术,更须去本土寻找成长的力量。虽然它的核心是东方文化,但它的成长模式并不只是固守着这样一个不变的传统,以此为成长基点。这样的话,东方电影也只能被人一直冠上老旧的名声。从先秦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演变,为何现在却让它墨守成规,核心的不枯竭正源于变与不变。它的变是依时所变,依境所改,它的不变是固有灵魂的固守,就像一捧水,今天把它放在瓶子里,它呈瓶子状,明天把它放在水杯里,它呈杯子状,它不管怎样更改它的形态,它依旧是那一捧水。守住这捧水,东方文化以此进行生发,或通过吸纳,或通过自我成长,或通过融合,它便会呈现出千千万万种面孔。作为传统的这捧水,它来自古代,来自被我们所抛弃的那些时代,但它穿过历代沧桑到达现今自有其不惧时间的价值,就算现今不再,它一定还会存在。也就是说,它会一直存在,一直生长,从古代到现今一直到未来。“……新东方主义……是一个主体,它是一种经过系统的整理与创新,逐渐形成的一种有机的重生,而且自然而然地融会在今天与未来的讯息之中。”通过它,我们能认识过去,看清现今,预见并创设未来,也就是说传统不仅仅属于过去,更不是“落后”“老派”的代名词。
同样,东方电影植根于东方,它拥有自己的成长轨迹与发展样式。东方电影真正的生长力量和永恒之美应该源自传统内里的力量,它需要有一副自己的骨骼和灵魂。
比如贾樟柯,他迄今没有创作过一部古装电影,但他电影里的观世观人方式有时却有着最东方的一面,在他的眼里,有些传统是不会死的,它换副皮囊依旧活在当下,活在芸芸众生之间。最典型的便是《天注定》,《天注定》的众人物与事件取自当下现实故事,而演绎方式却又类似古代侠义小说,最突出的便是小玉刺杀欺辱她的男人,从人物演绎方式到镜语气场,都俨然一股古代武侠气息,就像贾樟柯所说的那样:“我上网看到的东西(作者注:比如邓玉娇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跟我在六七十年代武侠片里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古代人骑马,现代人坐高铁,那种奔波,在游走里面寻找生活的生机的可能性,那种压力感、悲情都是一样的。”而“天注定”三个字本就是东方对人事命运的态度,他们行凶或者自杀自是他们命运使然,冥冥之中天注定。
虽然贾樟柯欣赏德·西卡、布列松、侯孝贤,但他的电影却谁的也不像,德,西卡、布列松帮助贾樟柯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认知社会的方式,或者是共鸣,侯孝贤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式,即东方人自己的观世态度,以及表现内容,即城镇底层青年。以东方的观世态度,以德,西卡、布列松的社会认知来观照当代城镇底层的时代变迁,這便是贾樟柯。这里的传统美是切实的伤感,这里没有“第五代”的东方传奇,这里有的是感物伤怀,而这物早已不是古诗词里精致的闲愁闺怨和不得志,也不是80年代影片“文人式”的伤感,这里的物是赤裸裸的粗粝现实,这里的现实是被拆后或淹没或颓败的奉节城(《三峡好人》),或者是任凭世事变动静穆的冰河(《山河故人》),这里有的是由时代变化阵痛所产生的东方式隐忍悲悯与包容。他对传统美进行了属于自己的变异,贾樟柯给予传统于质朴粗糙的当下底层现实,传统给予贾樟柯于悲悯现实残酷的无言静美。故事内容的当下现实,认知社会方式的现代性、开阔性,使灵魂深处的东方传统美呈现出别样的光彩。
二、自身文化的融构与生发
自身性与独立性并不是指狭隘于自身文化之中。文化的生长需要包容与吸纳,东汉末年,印度佛教传人中国,中国本土道教文化植入印度佛教形成禅宗,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才形成了今天的儒释道三重文化格局。或者像侯孝贤曾宣称的,“就像佛教(由印度传人的外来宗教)缓慢演变成为中国本土传统的一部分(起点是敦煌石窟令人赞叹的石刻),西方文化有一天也会变成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虽然要花上数百年时间”。东方电影也需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外来再强大的电影力量也只是一种暂时的助推力,如果这种力量没有被本土所吸纳、所融会,这种力量会很快消失;反之,则呈现出永恒性、持续性。
异文化参与的目的应该是提升自身文化,修复自身文化的缺陷,并以自身文化去修复所吸纳的异文化的缺陷。比如韩国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和《春夏秋冬又一春》都展现出了西方现代文明带给现代人的精神困顿,而化解这种困顿的方式之一却是传统亲情伦理与本土宗教:《撒玛利亚女孩》利用父女情,《春夏秋冬又一春》则利用佛教与师徒情。“用本民族的文化话语重新阐释这种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性价值,以传统文化的元素完成现代观念的内在重组,即,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换。”
虽说,想要吸纳的异文化一般看上去都是优于自身文化的文化,但如果用此割裂矮化长久积淀的传统,全盘用异文化拯救文化自身现状,造成的结果可能会是传统遗失,异文化的水土不服,成为邯郸学步,在世界文化上自然也没有什么优势了。就像李欧梵对新旧文化的看法:“晚清文化的特色不在去旧创新,而是在旧中翻新——旧瓶装新酒,逐渐满溢以后,才带动一种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乍看时并不显眼,但影响深远。”
东方镜像的成长自然也是如此,它需要一种融构,即将异文化融进自身文化之中,成为提升东方镜像的一种新鲜力量。就像金基德《春夏秋冬又一春》的“因果轮回”和《悲梦》里的“庄周梦蝶”,从一方面看,它是用东方语境阐释西方常表现的现代精神困境,从另一方面看,它则是用西方常表现的现代精神困境去化解东方传统命题的局限,使东方传统具有阐释表现现代精神的力量,从而使东方传统幻化出有别于以往东方传统,符合当代精神的美感与精神价值。
三、独立东方镜语体系的建立与受众培养
自电影诞生以来,巴赞、爱森斯坦、格里菲斯一直主导着电影语言,并且培养出了大批受众。可是,电影语言应该是多样的,东方文化自能培育出东方镜语,就像费穆的《小城之春》,它的镜语脱胎于中国古典戏曲与诗词,而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则根据日本传统卷轴画演化出不一样的长镜头,小津安二郎则根据日本传统生活习惯创造出“榻榻米影像”。最初,电影来自于注重写实与叙事的西方文化,比如巴赞的长镜头注重镜头的真实与暖昧,而爱森斯坦注重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意义性,格里菲斯则注重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戏剧性。注重写实的质感、主题意义的明显、戏剧的剧烈鲜明,这本都不是东方文化所擅长的,相反,东方更擅长抒情的缠绵与写意,更看重言有尽而意无穷,而这些需要东方文化自我孕育镜语来表达。
费穆在这方面是有开拓意义的,他的《小城之春》中很少有切镜头,但又不像注重写实的巴赞的长镜头,他很少切的原因在于为了营造东方文化里气息不止、韵味无穷的氛围。在费穆的镜头里,人物始终并不是孤立的,他(她)始终在周围人事环境或者自然环境中,他们的情感情绪也会借这人、事或自然环境来表达,这正表现出东方镜语的含蓄性。
侯孝贤也一直相信用他的东方信仰可以创造东方式的表达,只有如此,他的东方式情怀才能表达出来。所以他运用足够长的固定长镜头让镜头涌发出镜头时空里本身的静美,以体现东方情怀与韵味,所以他以足够远的远镜头让人与环境融为一体,以此来道出天地人式的东方式人生观,以及对人事浮沉的包容、悲悯、关怀,所以他以写意留白的剪辑叙事策略将电影拍成一首东方抒情诗,而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精彩迭出的故事。
相对于费穆与侯孝贤文人式的东方镜语,王家卫的东方镜语更具有时尚前卫感,这是因为王家卫的电影里都市感很强。王家卫经常用天空、流云、大雨、光线暗沉的都市街头、灯色昏暗的室内空间来表现影片的低沉情绪,有时画面还配上含蓄内敛的个人独白抒情画外音。手持摄影更是为了打破规则镜头对情绪挥洒的阻碍,让情绪情感自由喷发,直到饱满为止,同时它也符合都市躁动模糊的节奏。总的来说,王家卫的画面里始终含着一种迷离的情感,他的人物、故事似乎都是在为抒发这种现代都市里漂泊不定的情感而服务的,这是一种现代东方式的抒情。
由此可以看出,东方镜语是不同于巴贊、爱森斯坦、格里菲斯对镜语现实暧昧性、意义性、戏剧性的注重,它更像中国的古典诗句,言简意赅,以留白的方式表达出不止于该句诗该镜头的情怀,并以有限的表达创造出无限的怀想,也就是说东方镜语更注重镜语的抒情和体悟。
抒情是东方文化的特点,东方镜语以它为特点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性,但抒情自有抒情的弱点。东方镜语应该是丰富的,它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将戏剧性、意义性、现实暧昧性纳入自己的体系,以此来促进东方镜语的成长。
独立东方镜语体系的建立不仅仅需要创作者的努力,也需要受众的培养,可是观众早已习惯早前的镜语体系,换一种镜语体系是很难接受的。《刺客聂隐娘》叫好不叫座的原因就在这里,它的镜语是不同于先前的模式的,何况中国观影的大环境并不好,观众的电影素养还不够。就像从小就读诵古典诗词,自然不习惯西方诗歌,如果早先观众适应的是东方镜语体系,现在不适应的恐怕便是西方镜语体系了。
[作者简介]杜玉秋(1986- ),女,山东菏泽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