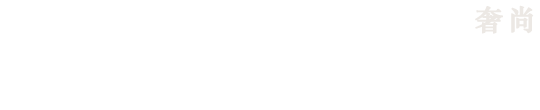[摘要]中国电影民间叙事在20世纪初随着中国本土电影业的兴起而成为中国电影中一道极为常见的风景线,在经历了“新时期”前的“政治化”叙说、“第五代”导演的“诗化”塑造、“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化”呈现以及“另类”导演冯小刚的“喜剧化”民间创作后,电影叙事空间的主体由乡村迁移到都市,在这种时代流转和叙事空间的迁移中,影像民间的呈现慢慢远离真实生活,最终成为电影叙事中一个常见而又不甚真实的消费符号。
[关键词]中国电影;民间叙事;乡村;都市
民间是个层次多维、寓意丰富的概念,明代以前民间寓指与官方、士族生活相对的庶民生活空间,是社会下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追求的指称,表达一种无拘无束自由生存的理想,略有与国家权力中心对立的指向,含有一定政治阶层色彩。在当代社会,民间是与体制、精英相映证的范畴,指向普通民众生活以及从中化育而成的一套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传统农耕社会庶民多居乡村,民间则是乡村生活的代言词,在当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乡村已被商业逻辑浸染,民间更多指向都市底层生活。作为一种叙事方式,民间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电影,从此成为中国电影中最常见的风景。
一、被政治化的空间:“新时期”①前中国电影民间叙事
1905年任庆泰在上海拍摄谭鑫培主演的戏剧电影《定军山》,由此拉开中国电影序幕,此后经历近20年艰难探索中国电影才在民族资本家和先进知识分子的通力协作下进入创作初盛期。当时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与军阀混战割据使民族资本实业投资很难获得相应回报,而第一批国产电影在市场上又引起了强烈反响收获了丰裕利润,电影因此成为民族资本投资的首选,商业利益的满足自然成为此时电影创作的主要目的。但当时中国院线各类硬件设施相对简陋,电影票价也比较低廉,观众主体为社会底层民众,为满足这一观众群体的审美需求获得票房回报,此时电影创作主要选择民间喜闻乐见的故事传说进行加工、改编。有取材于京剧的《五福临门》、昆曲的《呆中福》,来源于民间故事的《赌徒装死》,改编自通俗文学的《济公活佛》系列等;还有少量反映当时社会底层现实生活的《难夫难妻》等。在更好地引起观众共鸣以期收获更丰厚票房目的的牵引下,此时中国电影民间叙事相对比较贴近当时民间现实生活,价值标准以农耕文明中形成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为主。
1930年后,随着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民族斗争的日益尖锐,民族救亡与政治革命成为主要的社会文化思潮,“左翼”文化运动因之兴起,在当时具有较广泛影响力的电影自然也成为“左翼”文化运动要争取的重要阵地。1930年“左联”提出文学艺术“大众化”,以“政治”与“革命”为主题的“硬”电影也渐渐成为当时中国电影叙事主流,电影民间叙事以描绘城乡社会革命为主,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政治指意的“民间”电影,像《神女》《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此时电影民间叙事多以“革命”和“进步”为核心价值观,或描写底层民众被欺压的种种悲剧,或表现工人、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剥削阶层如何斗争。总体而言,此时电影民间叙事对表现都市还是乡村并无明显偏爱,“民间”更多指向其阶级性和与剥削阶级的对抗性,泛指所有被剥削和压迫的人们。进步人士试图借电影苦难民间的表述来唤醒观众的时局危急意识与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意识,鼓舞人们与黑暗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信心,这种以“进步”为导向、具有政治倾向的民间叙事此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成为20世纪中后期中国电影叙事的主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电影主力转战武汉,在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中电影叙事转入“国防电影”时代。1938年1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并发表宣言,希望电影能“深入军队、工厂和农村去”“服务抗战宣传”②。自孙瑜开拍《春到人间》始,便诞生了一系列反映中国民间社会抗战风潮的电影,如《好丈夫》《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等。此时电影民间叙事常以灰暗时代为背景,通过卑微人物面对国家存亡的表现来体现民间群体勇于牺牲的高尚品质。如果说左翼民间电影叙事在“政治化”民间生活时,还能以一定的艺术表现张力让观众无法回避生命价值、道德困境等问题的深层思考,那么抗战时期影像民间的表现已渐渐远离民间生活,带有强烈的政治宣教色彩,电影审美功能愈益让位于宣传功能。与此同时,在沦陷区上海另一种与“政治化”民间大相径庭的新市民电影悄然兴起,以桑弧和张爱玲创作的《太太万岁》为代表,它承续了早期中国电影关注世俗民生的传统,以平民视角去观察和审视生活,能相对真实地再现三四十年代中国都市民间生活。只是,新市民电影直到20世纪末随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和商业电影的再次兴起才开始影响新一代中国电影创作。抗战时期电影民间只是一个负载着培养“民族—国家”意识和强化抗敌信心的政治化指意符号,民间内涵指向“民族”与“国家”,是乡村还是都市,其偏好并不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受前苏联电影理论影响中国电影叙事仍强调政治服务功能的实现,与新中国成立前以影像民间表现革命的叙事策略有明显的前后承续性,电影中的民间呈现以讴歌革命战争、控诉旧社会、赞美新生活为主。出身草莽的英雄自觉进步是这一时期电影民间叙事的主要切入点,像嘎子(《小兵张嘎》)、王成(《英雄儿女》)、李向阳(《地道战》)等。影片中民间生活就是革命生活,个人情感隐没在大公无私的革命事业奋斗中。故而“十七年”电影虽然也出现了《南征北战》《红旗谱》《五朵金花》等优秀作品,但电影叙事中的民间呈现渐渐走向程式化、教条化的囹圄。而电影民间叙事对于乡村还是都市的选择则恰如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妻子张英虽然在革命胜利进城生活,但仍与乡村保持亲密联系,时时不忘以乡土价值观念来规约和改正丈夫的都市“小资”思想,电影中的民间叙事有着明显的乡村化倾向。
二、被史诗化的乡野:“第五代”电影的民间叙事
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渐渐成为中国话语核心,“现代化”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全面进入中国电影叙事。然而,当时中国社会对外来词汇“现代性”的理解与价值衡量不易达成一致,其直接体现即为电影界关于电影观念、电影语言如何“现代化”的论争。但是不管当时论争双方分歧多大,对“现代”的理解如何不同,却都一致认可中国“现代”生活的实现是西方文明在东方的呈现,因此向西方学习现代电影语言是时代需求。东方文明的典型表征——乡村成为“第四代”导演电影叙事的首选,他们以中国乡村生活去政治化的这一改变来凸显中国“现代化”的开始,由此出现了《海滩》《老井》《乡音》《湘女潇潇》等经典之作。在其电影民间叙事中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东方和西方的对立渐渐初显,但当时“现代化”于中国仍只是待将实现的梦想,导演们也不可能真正具备“现代”意识,与其说“第四代”开启了中国电影“现代”民间叙事的新篇章,不如说他们为行将逝去的农耕文明、乡村民间唱了一曲深情挽歌。
1984年陈凯歌的《黄土地》横空出世,他承续了“第四代”电影民间叙事的去政治化理想,并以历史的意蕴和写意的造型,将诗歌意象的象征性与电影叙事的情节性完美结合,打造了一个苍凉沉重的乡土民间世界。因缺少科学知识而滋生的“祈雨”场景和壮丽的“腰鼓阵”相融合,在无知的荒诞悲凉中又透着一种艺术的深沉。张艺谋同样沿袭了这种传奇式的乡土民间叙事,他的《红高粱》以村姑奶奶与土匪爷爷平凡瑰丽的人生来呈现西北乡村民俗的壮丽和社会的封闭落后,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里又浓墨重彩地刻画“点灯”“封灯”“洗脚”这些亦真亦假的乡土民间仪式,将知识分子对人性和民族命运的理性反思隐藏在充满奇观异象的乡村民间叙事中,表达他们对于民族文化反思和国族历史重构的梦想。
中国电影“第五代”作为一种从时代激变中浮出地表的文化现象,与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思想界“文化寻根热”的弥漫密切相关。对以启蒙为己任的他们而言,民间是文化苦旅的代名词,他们的电影已远离了对乡村民间生活表层意义诉说的追求,习惯以诗化的表达方式赋予“民间”和“土地”哲学意蕴,将“民间”提升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张艺谋曾如此阐释《黄土地》的创作初衷:“想表现人们从原始的蒙昧中焕发而出的呐喊和力量,想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而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想表现人的命运,想表现人的感情——爱、恨、强悍、脆弱,愚昧和善良中对渴望和追求……”③此时,“民间”已成为一种媒介,是承载了80年代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意识、用以表达个体对人生和命运永无休止哲学追问的媒介。他们通过这一媒介透视中国农民的悲剧性命运,剖析国民性格的劣根性,这种透视和剖析又只是为了击穿古老中国农耕文明的厚重和狭隘,重铸一个理性、文明的现代国家民族性格。因此,“第五代”导演的叙事视角是由外向里的俯视,创作者以引领者身份俯看“民间”的叙述,在电影叙事里民间作为噬待启蒙的“被看者”和“他者”,并不具备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影片中的民间叙事也不是现实民间的自我表达,是知识分子对古老中国文明的质询和对西方工业文明渴求与崇拜的隐喻式述说,他们期望通过中国乡村民间的苦难呈现来确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合理性,至此,乡村民间虽仍是中国电影的叙事主角,但已成为隐在幕后“都市”的陪衬者,乡村意味落后、都市喻指文明的价值对等关系逐渐形成。
三、边缘化的都市空间:“第六代”电影的民间叙事
十年之后,时值中国电影体制转轨之际“第六代”导演初入影坛,他们已经失去了国家资本这一强大后盾作资金保障,彼时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票房惨淡,也使影坛新人电影创作境遇雪上加霜。既没丰裕资金为保障,又难获得商业资本的支持,“第六代”导演只好选择小成本电影以搏出位。因此,他们的电影少有精良制作,也极少专业演员,以同代导演彼此客串为主,间或也请圈内熟悉的演员朋友担纲。从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看,“第六代”经历了中国社会与家庭关系剧变的创伤与迷惘,也体验了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传统生活模式崩溃的失落与欢欣。他们成长之时恰逢中国电影宏大叙事瓦崩之际,从容沉郁的历史叙事已成昨日旧梦,他们也愿意选择另一种更个性化的叙事来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故而,从叙事风格论,“第六代”电影的民间叙事不像前辈导演那样具有某种艺术的“共性”,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一概而述他们整体的风格。只能大概言之,他们习惯于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喜欢选择纪录片式的写真讲述,以略带感伤犹疑情调的碎片式叙事,传达一种迷离驳杂、动荡不安的现代都市体验。
如同《苏州河》中无名摄影师所说:“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第六代”电影的民间叙事“就是以边缘人出现的对于中国底层生活的高度关注,就是企图通过影像建构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普通人生存状态的记录历史。”④他们试图以摇滚歌手、先锋艺术家、北漂艺人、都市外乡人、妓女、小偷、民工等各种“边缘人”来建构一个处于非正常状态的都市“异化”民间,以尖锐的社会矛盾、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和民间个体的沉浮人生来映射那些因为体制规约而被漠视和遗忘的底层“灰色”现实。贾樟柯的《站台》最具代表性,在社会急剧变化中青年民间文化工作者身份从文工团员转化成流动帐篷表演队员,最后不得不接受烟消云散的结局。在“第六代”的民间叙事里不论是普通工人(《卡拉是条狗》)、青春期少年(《十七岁的单车》)、还是新生代都市青年(《北京杂种》)都处于一种与主流社会断裂的态势,他们恶劣而混乱的生存环境,虽然卑微却依然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使其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体制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态势。
正是由于“第六代”电影民间叙事边缘化的视角选择,类纪录片的写实主义风格,以及民间叙事在扭曲与破败中隐藏的与体制的对抗性,暗合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政治立场,也满足了西方世界习惯的“东方”想象——在专制统治下人们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悲惨生活,“第六代”因此赢得了西方电影节的青睐。当然影片获奖收获的并不只是对电影“艺术”表现的认可,还有价值不菲的奖金收入,这笔收入可以缓解电影前期资本投入的压力。于是“边缘”民间叙事与西方电影节获奖互为动力,成为“第六代”导演缓解电影创作生存困境的拯救性力量。对他们来说“民间”叙事是用来确证自己作为电影人主体性的工具,民间的主体性表达并不是他们叙事的目的。故而与其说他们在电影中展现了当代社会民间生活,不如说他们以弱势的边缘化民间叙事为载体,为自己攫取了电影创作的第一桶金,确证了自己电影风格的形成。他们的电影民间叙事虽然也隐含着对抗性,但已从乡村与都市寓言的落后与文明的文化性对抗,转而为更注重民间与体制的政治性对抗。对于这些成长在现代中国,又接受过严格专业化教育的“第六代”来说,乡村生活经验已是一种空白和缺席,他们的电影叙事里都市民间是主角,乡村民间已经淡漠成天边一抹遥远的影子模糊得几近不见。
四、另类的“真实”:香港喜剧电影与冯小刚电影民间叙事
当中国内地电影尚在艺术化的追求中寻根民族文化时,香港电影却沿着电影的商业属性走向了娱乐化时代,喜剧电影是80年代香港电影的主旋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成龙的功夫喜剧与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成龙以“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为主题,讲述市井生活中出身平凡的“乡巴佬”们,如何凭借自己超群的武力和人格魅力战胜恶势力的故事。很难说成龙电影的民间叙事呈现了当代都市民间生活,他的民间更多的是中国传奇小说中武侠“正义世界”的现代转化,民间生活其实只是一个隐性背景,真正得到彰显的是“民间”作为正义世界所蕴藏着的惩恶扬善的侠义力量。只是这种侠义力量的实现常常需要依赖民间英雄们敏捷的身手,而这种深厚的武侠功夫本身就是一种虚幻性的存在,其民间的真实就更难确证。周星驰的民间叙事虽然常以小人物为主人公,如好色小警察(《咖喱辣椒》)、被人百般歧视的卧底警察(《逃学威龙》)、受尽人情冷漠的乞丐(《武状元苏乞儿》),但他在电影中极力放大的是电影的喜剧特性,由此使得民间以一种极为荒诞的方式呈现,他从不介意提醒观众电影民间的虚拟性,甚至故意以穿帮的方式制造笑点以达到喜剧效果,像电影里随处可见峨冠缚带的古人满口英文、做着汉堡,发明功能古怪的手枪、电吹风、剃须刀等。他的电影民间叙事其实只是一个离析正统、消解崇高和意义来娱乐观众,以博取观众注意力的怪诞符号。
但是恰恰因为成龙电影民间叙事中的正义暴力幻象补偿了现实民间生活中人们的心理失衡,满足了在政治、权力与金钱多重挤压下普通人凭借个人能力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梦想。周星驰的怪诞喜剧民间娱乐了身处社会剧变中不知所措的观众,他们在90年代的中国内地收获了不菲的票房,也引领了内地贺岁喜剧电影的风潮,学习最成功的是冯小刚。他从90年代末的《甲方乙方》开始,近二十年拍下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手机》《大腕》《天下无贼》《非诚勿扰》《私人订制》等十多部喜剧电影,无有败绩。他认为:“电影的魂应该扣在普通人的梦想、普通人的烦恼上”,“淋漓尽致地把老百姓过日子的那点事给剥开,一层一层地剥开,这种一定会抓人。”⑤因此,民间的呈现成为冯小刚电影的灵魂所在。但他同时又认为“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觉得特别开心地度过一个多小时,这是我们拍电影的一个根本目标”⑥。故此,冯小刚修正了香港电影民间叙事的虚幻性和怪诞性,在表现都市小人物真实情感欲望和生活追求的同时不忘制造“笑点”,在观众最熟悉的平凡生活中制造“笑点”时,又不会忘记将人们在传统社会生活空间崩溃、价值观念瓦解后的迷茫失落与焦虑植入其中。相较于其他导演电影民间叙事因刻意雕琢而出现的“失真”,冯小刚电影中的民间叙事反而更贴近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在那些看似虚拟离奇的情境幻象中能相对真实地反映时代的众生世相。
90年代末“都市生活”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图景,即使在最遥远的乡村“消费”与“现代化”也已成为乡村生活的主旋律,电影民间叙事的空间主体自乡村而迁移到都市也属应然。并且,因90年代中国电影商业属性的重获重视以及随之而来电影创作对观众兴趣爱好的关注,乡村民间叙事在中国电影叙事中已渐渐沉寂难得一见。不可否认在当代都市民间喜剧电影创作中民间确因消费和资本的介入而获得了一定表达空间,但同样在电影的商业化运作中,民间的表述也不可避免地会以逐利为导向,只有能获得商业利益的民间表述才有可能在电影中得到充分表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相对真实的冯氏民间叙事在真实中又不免透露着几分虚无。总而言之,中国电影民间叙事在经历了“新时期”前中国电影的“政治化”民间叙述,“第五代”的“诗化”乡野塑造,“第六代”的“边缘化”都市呈现以及另类导演冯小刚的“喜剧”民间创作后,叙事空间主体已由乡村迁移到都市。在这种时代流转和叙事空间的迁移中,电影民间的呈现慢慢远离真实生活,在消费逻辑的主宰中最终成为一个常见而又不甚真实的影像符号。
注释:
① “新时期”主要是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从教条思想束缚下解放的文艺创作时期。
② 《抗战电影》创刊号,汉口出版,1938年3月31日。
③ 张艺谋:《黄土地摄影阐述》,《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④ 蓝爱国:《后好莱坞时代的中国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⑤ 谭政、冯小刚:《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1期。
⑥ 张玲:《走近冯小刚》, 《电影通讯》,1999年第6期。
[作者简介] 邹欣星(1981— ),女,湖南涟源人,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大众传媒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