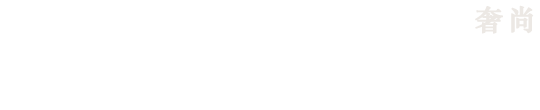李新华+贾奎林
[摘要]我国后现代文化所处的文化对于国家和市场的“二主一仆”的社会情境使得作为后现代文化表现形式的媒介文化建构面对诸多价值选择的困境。突出表现为当代以现代性建构定位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在价值理性方面表现为面对人类理性价值的极强的反叛精神和多重解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作为世纪初叶特殊文化情境的后现代文化产品,表现出强烈的传统价值回归、意象表达扭曲以及艺术运作的过度商品化特征。
[关键词]解构与重构;危机与错乱;过度商品化
李少红版电视剧《红楼梦》“后现代”特征批判
作为“后现代主义”中心词的 “解构主义”伴随后现代思潮,于20世纪末叶以大众文化形式现身中国内地,并在与“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博弈中,日益凸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当代中国这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无序杂存的文化形态中,大众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兴盛使得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发生重大倾斜。然而,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解构并不表现为西方解构主义的反叛理性、反叛现代性,而更多地表现为结构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重构”,抑或是“再结构”。
李少红版电视剧《红楼梦》解构了《红楼梦》原作价值蕴涵的民主性精华,重构的是为现代社会所鄙弃的封建性糟粕,建构的是作为后现代主义技法存在的“碎片性”形式。李少红打着忠于原著的旗号拍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却以程伟元百二十回本为蓝本,其本身就是对原著意义主旨抑或是对曹雪芹创作初衷的背叛。曹八十回残本《红楼梦》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主旨,以“宝黛悲剧”揭示封建礼教吃人本质,以“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隐喻封建制度的彻底灭绝,表现出明显的“解构”特征。而高鹗续违背原著创作意图,以“金玉良缘”取代“宝黛悲剧”,以所谓“兰桂齐芳”妄图延续封建礼教的辉煌,以“世道轮回”这种封建蒙昧观念遮盖曹雪芹对中国封建礼制的血泪控诉和悲情批判。李少红以百二十回本作为蓝本拍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本身就意味着她选择了“解构”曹雪芹,也意味着对中国近现代百年民主革命价值诉求的“解构”与背叛。而其重构的则是对传统价值理念的迎合与回归,并且这种“回归”与“迎合”于新世纪初叶的经典电视剧改编的“流行”已成不争的事实。新版《三国演义》以当代政治权谋哲学诠释三国故事被誉为“时空穿越”的代表。新版《水浒》也让好汉们围上围脖,以显示其儒雅;让作为“造反英雄”的他们摆脱了草莽之气,转而成为执著于“忠孝节烈”的家国栋梁。
后现代影视艺术以传媒技术的充分发展为前提,通过弘大的场景、华丽的画面、精湛的表现技法营造瑰丽的艺术情境。如果说形象化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并不导向或表达某种意义的话,那么,新版《红楼梦》在华贵展示的背后流露的就是意义的“错乱”,甚或是“空洞”的炫耀,乃至于是欲望冲动的毫无遮盖的隐喻与挑逗。宝玉梦中的秦可卿妖艳近娼,飘移似鬼,音乐诡异、惊悚,气氛的营造远远超越了影像所应承载的理性意义,悲情隐喻反倒成就了导演的隐秘心理宣泄。在执导过程中,导演在忠于原著的语境中过多地移植了自己的主观价值理念,把以“哀婉、寂灭”为主题皈依的华夏经典编排成了“虚伪,华丽”的韩剧,而这两种文化理念的价值内涵却又是大相径庭的。《红楼梦》小说文本尽管是悲剧叙事,却不失雍容华贵,叙述的是华夏贵族主体价值失落后的莫名悲哀;而韩剧所彰显的是殖民地文化的虚假繁荣,无法掩饰的是主体价值虚无的空虚和无聊。后现代主义艺术是一种复制摹本的艺术,新版《红楼梦》则成为复制摹本的集合体,且摹本与摹本间出现了意义表达的割裂与矛盾,甚或是逻辑表达的混乱。首先电视剧文本展现给受众的与其说是一部影视作品,毋宁说是当代影视表现技法的大杂烩。昆曲的铜钱头和中国画的写意表达,画外音与漂移展示,鬼魅音乐与明星阵容,所有这些表现手法如果运用恰当无不各具魅力,而无规则的拼盘式炫耀则无疑会破坏艺术作品的整体意蕴。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最透彻的理解,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无情的商品化的最终结果。” [1]后现代特征明显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无疑也是将文化艺术加以商品化的结果。这种文化商品化的运作无论对于经典本身,还是对于受众,乃至电视剧的操作者和参与者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从2006年开始的“‘江中亮嗓唤醒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活动的成果是多方面的,但所有的都是利于市场的,从来就没有利于艺术的。首先,选秀活动以及有关选秀活动的炒作和丑闻极大地激发了受众对于新版《红楼梦》的心理期待。过于强烈的选秀刺激使得人们对于电视剧的期望值过高,而新版电视剧内容与受众既有心理结构图式间的巨大差距则远远超过了受众所能承受的心理极限。同时,这种高调选秀活动本身也有违艺术创作的“陌生化”原则。新版《红楼梦》给人的感觉与其说在播电视剧,毋宁说是《红楼梦》秀场的继续。选秀运作还人为地造成演员与角色的巨大错位。真正具备演绎红楼梦中人,具备相当精神涵养和艺术造诣的适合人选是不会也不屑于参加此类所谓选秀活动的,如此就很难说有适当的演员来演绎新版《红楼梦》。于是乎,就出现了胡玫导演的愤然离去,也就有了李少红导演的“乱点鸳鸯谱”。而这一切又无不与当代的市场与人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进入剧组的不是“花过钱”的,就是“结过缘”的。所以说这个由“金钱与人情”编织起来的剧组,在我们这个“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时代所“制造”的所谓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也就只能是个“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的消费产品,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艺术品。
我国媒介文化的“后现代”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始终在中国后现代文化建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使得后现代文化在中国处于“‘文化—国家—市场三方语境而非在西方的‘文化—市场二元语境,出现了文化面对经济和政治的‘两主一仆的现实景观”[2]。20世纪末叶,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初期发展可以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阶段。80年代以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的兴起与90年代以影视媒介产品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的大发展尽管都以大众文化的形式出现,背后却有着迥然各异的社会文化背景,但二者却无不留有国家政治走向的烙印。80年代初期,在刚刚经历“文革”的特殊语境下,大众文化的流行,本身就是对毛时代以“革命”为圭臬的左倾文化意指的悖逆与否定。尽管当时以港台流行歌曲为代表的文化作品已经具备了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消费性特征。此时期我国大众文化的形成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但也不能否定其间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西方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大众文化的浸淫既填补了由否定“文革文艺”所造成的文化真空,同时也为国家在社会文化层面否定“文革”提供了精神支撑。90年代,作为中国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影视媒介首先发起的是解构“神圣”的世俗化运动,表现为强烈的非道德、非艺术甚至非审美的现象特征,但其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它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两件大事,即所谓的“政治风波”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超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基本走向。“20世纪80年代国家权力系统和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有时甚至形成激烈冲突,但两个精英集团的相互依赖却是根本性的”[4]。这就决定当时作为后现代文化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的价值诉求依然是源于“五四”的启蒙与理性,其实质仍然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题中之义。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降临,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容和物质依存发生了重大改变。市场完全改变了“文化—国家—经济”的社会基本架构,国家政治与市场的合谋使得以文化精英存在的知识分子处于尴尬的境地,文化也就蜕变为经济的附庸,政治的奴婢,丧失了其作为公共空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定位使它成为政治游戏的道具,不同的价值主体通过大众文化的“解构”形式发泄着烦闷与抑郁,同时也在无形中建构着自身想往的无聊与神圣。于是“启蒙”变成了游戏,革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骚乱”;人民成为后现代意义的所谓“群氓”,自然也就成为可以愚弄的对象。新版电视剧《水浒》消解了原著对时代社会矛盾的揭示以及解决问题的“革命性”探寻,而妄想在世俗伦理、个人恩怨,乃至原始的“性”规则方面探讨所谓形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路。认为“母夜叉”孙二娘的“嗜杀”不是源于社会的逼迫,而是源于子虚乌有的“轮奸事件”。矮脚虎王英的食人心肝和孙二娘的“人肉馅”包子也仅仅是“说说而已”,而宋江对阎婆惜的“义举”也就成了始乱终弃的“一场游戏”。以国家政治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使得中国后现代文化的伪精英化、去精英化特征变得更加明显。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赋予大众的历史使命是“和平与发展”,抑或是“解构与消费”,主流意识形态操纵国家机器正在消解着大众的革命意义,乃至其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大众本身。中国当代大众文化解构的是“启蒙”,消解的是“意义”,制造的是“麻木与虚无”。
中国的后现代思潮是作为某种现代性的特殊实现方式出现的,是对中国百年现代性的“解构”与“重构”。我国当代以现代性建构定位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在价值理性方面表现为面对人类理性价值的极强的反叛精神和多重解构。首先,面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国家主流价值观予以明确的抵制与否认。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原旨继续革命,显然与当代社会主流利益集团价值诉求相背离。或者回归传统贵族统治社会秩序,则无疑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的初衷。新时期以来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策略调整就是推崇以“庸俗化”为主要特征的、以人类原始本能为依归的所谓“人性至上”原则,这也就是中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在这种“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媒介文化中,影视叙事从现实与历史的限制中摆脱出来成为投射受众勇气、智慧,实现其光荣与梦想的文本。“受众在新的叙事文本中的情与爱、生与死、沉与浮的故事之中释放着被抑制的潜意识,满足着在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的弗洛伊德所谓‘快乐原则”[5],而民众的理性意识则在无意识间被关进了价值虚无的“铁屋子”。
[参考文献]
[1] 吉姆·柯林斯.电视与后现代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32.
[2] 陶东风.国家—市场—社会:中国文化市场化的三方语境[J].文艺研究,1998(04).
[3] 金元浦.重新审视大众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2000(06).
[4] 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EB/OL].北大—重大法治研究中心,http://jus.cqu.edu.cn/index/2010/0411/425.php/2010-4-11.
[5] 陈立旭.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历程审视[EB/OL].文化研究,http://www.culstudies.com/plus/view.php?aid=1662/2003-10-4.
[作者简介] 李新华(1972—),女,河北邯郸人,廊坊师范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贾奎林(1969—),男,河北邯郸人,新闻学硕士,廊坊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