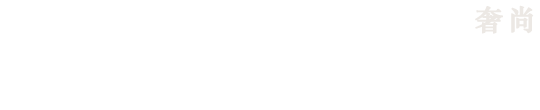[摘 要] 当代中国女性导演的电影创作是中国电影的一道独特风景。她们的影片在女性情怀的影像书写层面经历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觉消隐,到新时期的自我彰显,再到新世纪仍然无法摆脱的女性困惑的曲折历程,无不彰显着女性导演对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关注。中国女性导演用影像描绘了一部中国女性的心灵史。同时,新世纪女性导演在电影与市场的裹挟中也逐渐走向创作转型,不仅继续着电影中女性主题的探索,而且拓宽了女性导演在市场环境下的创作空间。
[关键词] 当代中国女性导演;女性意识;女性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文理学院文艺学重点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
当代中国电影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分别在新中国的“十七年”时期、“文革”后的新时期和21世纪前十二年的三个阶段描绘了恢弘的电影历史图景。其中,女性导演因其性别身份的特殊性,为中国电影注入了别样的视听韵味和意涵表达。无论是王苹在《柳堡的故事》(1957)、《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对女性传统情怀的抒写,还是黄蜀芹在《人·鬼·情》(1987)中所触及的女性自我的初次觉醒,甚或徐静蕾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2004)及李玉在《二次曝光》(2012)中呈现的女性无从挣脱的精神羁绊,无不彰显着女性导演对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关注和表达。本文将视点聚焦于当代中国电影女导演的创作,分析其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变化,并尝试阐述这种变化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关系。
一、女性主体的自觉消隐
在新中国初期的工农兵电影银幕上,女性作为性别主体的呈现处于缺席的状态。“女性形象不再作为男性欲望与目光的客体而存在,她们同样不曾作为独立于男性的性别群体而存在,更不可能成为核心视点的占有者与发出者。……男性、女性间的性别对立与差异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代之以人物与故事情境中阶级与政治上的对立和差异。”①银幕上的女性确立自我定位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被侮辱被损害,最终成为被权威拯救的对象(如喜儿),二是成为被男性同化的意识形态询唤对象(如江姐)。同时,以男性形象为主导的新中国银幕世界充溢着激情四射的阳刚之气,而女性的阴柔之美则被弃置于被批判和被否定的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框架下,附着在以“女特务”为代表的反面人物形象建构体系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正面女性形象则以去女性化的中性姿态为原则来确立银幕上的女性道德楷模。在革命叙事的话语模式下,影片中的女性必然将自我完全献祭于崇高的革命事业,自觉选择将女性的性别意识置于消隐的状态之中。
值得欣慰的是,“十七年”时期的部分电影作品仍试图在既定框架下寻找女性形象的突破。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在女性气质的保留上一定程度地突破了意识形态禁忌,那么在《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作品中,女性的传统形象则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呈现。《柳堡的故事》中,“英雄救美”的故事内核巧妙隐藏于革命叙事的话语模式下,使副班长和二妹子的爱情充满了好莱坞式的浪漫色彩,在同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中可谓独树一帜。同时,影片洋溢着东方式含蓄内敛的气质,将二妹子情窦初开、欲语还休的少女情怀展现得细腻动人。然而,女性的个人命运及自我实现都是在男性的拯救和引领下得以完成,实则暗合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男权体系之下的性别表述逻辑。只有当女性以革命者(民兵船队队长)的身份重新确立自身与男性身份(部队李连长)同等的价值认同之后,个人情感才能合法实现。
在王苹导演随后的创作中,女性形象开始由少女成长为伦理关系中的成熟女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当李侠与何兰芬之间从工作伙伴转变为夫妻关系之后,何兰芬的主体身份从单纯的革命者转变为妻子和母亲。虽然她的形象开始从前线转向后台,成为丈夫革命工作的后景,但女性在家庭中和工作上的重要作用却更加凸显。影片集中表现了她对丈夫工作的支持,对孩子的照顾以及在丈夫入狱后独自承担起家庭和工作的全部重担。革命者、妻子、母亲的多重身份建构起何兰芬作为女性主体的全部内涵,并将伦理范畴中的传统女性美德与革命话语相结合,共同确立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之下的男性道德标准则通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陈喜和春妮之间的情感危机得到充分的体现。陈喜丢弃艰苦朴素的传统,产生喜新厌旧的不良思想,与传统戏曲中陈世美忘恩负义的桥段有着一脉相承的伦理意义。这一点从老班长的话中可以窥见端倪:“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她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影片将春妮的个人情感失落归咎于陈喜的误入政治歧途,将“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传统伦理观念巧妙包装于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之下,并以春妮的政治完美等同于女性的道德完美。传统道德观念体系之下的女性形象经由革命叙事的话语模式跃然于银幕之上,呈现出这一时期颇为难得的女性之美。
在上述作品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显然被自觉遮蔽,取而代之的是对意识形态权威的彻底臣服。在这一创作前提之下,女性导演与生俱来的对女性的细腻关注仍然潜藏于影片的叙事机制之中。
二、女性意识的自我彰显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电影艺术观念进一步解放,中国电影创作也开启了新的文化空间。女性导演的创作才华喷薄而出,在广阔的创作平台上呈现了不少佳作。以史蜀君、张暖忻、黄蜀芹、彭小莲等人为代表的女性导演群体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创作团队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的影片不仅在电影语言的创新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而且在影片内涵上蕴涵着丰富的女性意识,传递着深邃的理性思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观念的革新和进步。
“作为一个女性,要想被人瞧得起,首先就要在事业上站得住,要有超强的自信心才行。”这是在影片《女大学生宿舍》(1983)中,匡亚兰在面对女性应该“做居里夫人还是贤妻良母”的选择题时的回答。影片虽然是一部以女大学生校园生活为表现对象的青春题材作品,但已经触及到女性对于自身在未来社会中的自我定位的思考。女性的性别独立意识已经初露端倪。如果说《女大学生宿舍》《沙鸥》(1981)等影片只是以女性人物为代表,传递着新时代下新一代青年人的新思想、新气质,那么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则完全以女性主义为视角,将女演员秋芸浓墨重彩的一生作为探询女性个体命运的终极范本。“这是一份当代中国女性的自况,同时也是一份隐忍的憧憬与梦想:渴望获救,却深知拯救难于降临。”②秋芸被男性主导的世界放逐,却也决绝选择了放逐男性,转而执著于在戏剧舞台上扮演钟馗,并由此获得心灵和灵魂的归依。这是女性的自我垂怜,也是女性对自我主体的有力书写。
女性意识的萌动与彰显是新时期以来女性导演创作的主要特征,用电影影像传递女性情怀的深思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以后。彭小莲的“上海三部曲”(《上海纪事》1998、《美丽上海》2004、《上海伦巴》2006)分别选取不同历史时期下的戏剧空间,呈现女性的生命际遇、情感体验与人生况味。值得一提的是,彭小莲导演的另一部佳作《假装没感觉》(2002)更鲜明地表达了创作者对女性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关怀。影片通过三代女性对待生活和处理情感的不同态度,探索现代都市女性的困境和焦虑,为争取独立人格的女性追求摇旗呐喊。历史向现实的渐次过渡,传统与现代的交替更新,都在女性的成长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社会对于女性的价值定位不断发生变化,而电影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彰显则显示了女性在现代社会新的文化环境下寻找自我价值认同的努力。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电影银幕上,女性导演的创作在宏大叙事的创作风潮之下独显一份小家碧玉般的似水情怀。她们不仅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女性的个体命运上,而且凭借女性的细腻与敏感试图把握社会时代变化的脉动。宁瀛的“北京三部曲”(《找乐》1993、《民警故事》1995、《夏日暖洋洋》2001)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三段小故事中再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变化以及都市化进程带给都市人的虚无感。可以说,“北京三部曲”是一个关于祖父、父亲和儿子的故事。老韩头代表的祖父一代,本该在退休之后享受“夕阳无限好”的晚年,却在格格不入的时代潮流中想要寻求一份老来自在的安宁而不得;民警李国力的生活完全被工作占据,然而片儿警的工作内容却堪比社区居委会,抓狗打狗成了工作的重心;出租车司机德子在熟悉的都市中漫游,寻找着一个又一个猎艳的对象,最终却发现,他仍然是一个只能与打工妹相匹配的底层人。都市的现代化进程在飞速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然而老一代人内心最向往的精神家园,已然留在了过去的历史中,随着都市森林中钢筋水泥的到来而远去,青年人还在浑噩的生活中摸索,却已经必须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给他们带来的重重打击。宁瀛的创作展现出女性导演少有的刚性气质,将一个时代远去的伤感和新时代来临前的阵痛描摹得入木三分。
三、无法挣脱的精神羁绊
新世纪以来,资深女性导演的创作仍在继续,新生代的中国女性导演群体也奉献出了一系列风格迥异的佳作。在国产大片横扫影坛的背景下,李玉、马俪文、徐静蕾等新生代女性导演以细腻温婉的女性姿态将一系列小清新文艺影片呈现在观众眼前,让人们在享受视觉大片的饕餮盛宴之后,也能感受到中国电影丝丝柔情的怡人之美。
与新时期女性导演的创作轨迹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女性导演的创作趋于多元化,不仅关注女性的外在生存状态和个体命运走向,而且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女性的潜意识心理和情感深处的隐秘世界。其中,2005年的《红颜》和《我们俩》秉承了八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用朴实无华的镜头语言诉说着女性命运和情感困境。《红颜》中小云的意外怀孕成为她永远无法摆脱的原罪,由此带来的巨大阴影始终伴随着她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世界。然而正是由于这次错误所诞生的孩子小勇,却照亮了她灰暗的人生,成为她生命中的一束希望之光。影片用颇具话题性的“母子恋”为噱头,实则传递出创作者对成年男性世界的绝望——女性在心理上能够依靠的,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弥漫全片的阴郁伤感和悲观情绪是女性挥之不去的心灵枷锁。相比之下,《我们俩》要显得温情许多。影片完全搁置男性,只把探讨的重点聚焦在女性之间的情感沟通上。创作者采用了封闭的室内剧拍摄手法,用戏剧空间的营造来表现小马和房东老太之间的情感冲突与和解。
导演李玉的电影向来以写实主义的影像风格和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而备受关注。2007年的《苹果》可以说是《红颜》的姊妹篇,延续了女性在男权世界中的悲剧命运的写照。无论是对小云还是刘苹果来说,男性的自私自利和不负责任是造成她们命运悲剧的主因,而她们只能选择被动接受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一切不公。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小云和刘苹果这样的底层女性身上并未显现,她们饱受其苦却不知如何挣脱。对于《红颜》的结尾设计,李玉曾给出这样的解释:“我的电影是希望平等的把我自己放到电影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命运,可能我跟片中女主人公一样迷茫,就像片尾小云出走一样,我其实一样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只是把这个状态呈现出来了。”③导演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将女性的苦难呈现出来,却没有为女性的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指出一条可行之道。
这种迷茫和不可捉摸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她在2012年的新作《二次曝光》中。这部影片可以说是李玉试图将艺术探索与商业包装相结合的一次大胆尝试。如果说,李玉在之前的创作中擅长将女性的外部苦难用写实主义原则进行表述,那么《二次曝光》的镜头则深入到了女性内在的精神世界,采用现代主义的描绘方式表达女性的内心焦虑。影片的表层叙事其实是主人公宋其内心世界的外在表述,她的幻觉被编织成一部带有悬疑色彩的心理剧而显得别具一格。宋其在童年和少女时期所经历的家庭变故和情感挫折给她带来了深刻的心理阴影,进而引发了她的失忆和幻想症状。“背叛”和“离开”是造成宋其精神困扰的两大主题。母亲对父亲的背叛以及由此带来的母亲的离世、父亲的再次离开、养父的意外死亡,让她的现实世界彻底崩溃了。只有在自我编织的幻觉世界里,她才能找到内心的依靠。然而,过去的历史如影随形潜入其中,让她无处可逃。影片在结尾处的设计颇为耐人寻味。宋其恢复记忆,找到了存放父母骨灰的溶洞,并且再次见到了曾经的恋人刘东。宋其的生活看似重新回到了正轨,然而出现在她眼前的是远方的海市蜃楼,还有身边童年时期的自己。恋人的回归并没有让宋其从过去的创伤中解脱,甚至这种逼真的幻觉反而使她陷入到另一个更加迷幻的世界中去。女性在心理和情感上的伤痛无法借由男性的帮助获得痊愈,也无法找到自我治愈的良方。
如果说李玉导演的创作将女性放置在一个绝对弱势的地位,去描绘一个柔弱女子的悲惨世界的话,那么,作为一名已经获得社会认可的知名演员,导演徐静蕾则在她的作品中彰显出一种强势女性的自我定位。然而,这种强势和女性独立的背后,潜藏的依然是对男性世界的崇拜和依赖。在她的处女作《我和爸爸》(2003)中,影片设立了一个“无母”的家庭结构,讲述了在男性(父亲)扶助之下的女性成长史。徐静蕾饰演的小鱼既是女儿,也是母亲。这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伦理身份设置。作为女儿,小鱼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追随男友去了上海,一年后却独自带着未出生的孩子回到北京;身为母亲,完全不懂如何照顾刚出生的孩子,面对孩子生病却只能求助老鱼。影片最后,小鱼已然成长为独立坚强的母亲,独自带着孩子,同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完成了独立女性的华丽转身。男性虽然成功隐退,但其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却在女性的生命中永远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徐静蕾的第二部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2004)对这一关系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女性已然完全迷失在对男性(或曰自我编织的爱情幻象)的极度迷恋中,更遑论人格独立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所谓的爱情面前,她可以让自己卑微到没有底线。女性的生命、尊严都随着对方的不屑一顾而变得毫无价值。“她宁愿受奴役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以至在她看来这种奴役表现了她的自由……她通过她的肉体、她的情感、她的行为,将会把他作为最高的价值和现实加以尊崇;她将会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虚无。爱对她变成了宗教。”④受虐式的爱情信仰者,必须通过奉献和牺牲,才能找到自我的存在感,并以此作为女性自我强大的基础。然而这种所谓的自我强大,只是女性自我麻醉的幻象而已。尽管创作者一直试图通过女性自强自立的强势形象来建立女性独立人格的正面价值,实际上却走入了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进而重复和巩固了男性主导地位的表述。
在徐静蕾之后的创作中,这种矛盾、困惑的心态时有表现,并通过《梦想照进现实》(2006)中的女演员之口进行了抽象化的表达。徐静蕾的本色出演正是她基于自我意识的迷茫而选择的宣泄出口。影片上演了一场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展开的关于梦想与现实、艺术与人生的思考和辩论,既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索,也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与前作相比,《梦想照进现实》明显超越了女性意识的范畴,上升到对人类自我存在的终极思考,将女性困惑这一主题纳入到更具普遍意义的存在主义范畴中进行探讨。
回看半个多世纪的女性导演创作,对女性情怀的影像书写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觉消隐,到新时期的自我彰显,再到新世纪后仍然缠绕于心的女性困惑的曲折历程。中国女性导演用影像描绘了一部中国女性的心灵史。近两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环境的变化,新生代女性导演的创作开始向商业化制作模式靠拢。李玉作品的明星效应,徐静蕾的都市爱情片尝试,都体现出创作者与观众之间达成的妥协,同时映射出女性导演的创作可以具备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中国电影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当下,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女性导演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注释:
① 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② 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③ 关雅狄:《跟李玉谈〈红颜〉(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f3ea3010001sp.html。
④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页。
[作者简介] 李静(1981— ),女,湖北老河口人,电影学博士,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