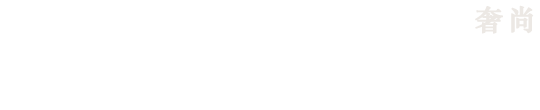[摘 要] 本文以上海“孤岛”时期古装电影滥觞中出现的女英雄形象为研究对象,将女英雄分成侠女、沙场红颜两种类型,分别从性别悬置、性别置换两个角度解读古装电影中所展现的个性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冲突,而对这对冲突的有效解决方式即为将个性消解,将性别置换,使个性意识绝对归属于国家意识。女性形象在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隐喻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并服务于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动员。
[关键词] “孤岛”电影; 女英雄;性别;民族国家认同
1939年上海电影中出现的古装片热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于1939年2月完成上映的古装历史片《木兰从军》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在上海连映85天,创下空前纪录,由此引发众多电影公司纷纷投资拍古装片。继《木兰从军》之后,出现了《武则天》《费贞娥刺虎》《葛嫩娘》《董小宛》《香妃》《梁红玉》《红线盗盒》《赛金花》等古装片。细细分析这些历史片不难发现,影片均以女性为主角,而讲述的都是女英雄故事。
关于对“孤岛”上海古装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有慈祥的《论抗战时期“孤岛”电影中的妓女形象》一文,该文章认为妓女形象的塑造达到了政治与商业的巧妙衔接。①
慈祥的这篇文章中沿袭了之前学者对妓女形象的关注,并指出妓女形象的塑造在特点的时代发挥特定的作用,但忽视了女性形象的改变②所包含的性别身份的建构。可以说 “孤岛”时期古装片中大量巾帼英雄热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最表层表现为《貂蝉》《木兰从军》的票房成功引发了制片商对类似题材的挖掘,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对成功影片的仿制,虽然很多影片有粗制滥造之嫌,但对上海电影产业的恢复以及保持中国电影的发展与繁荣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二层意义可以归结为保家卫国的故事取材于历史,可以躲避当时严苛的电检制度,成功上映有利于节约商业成本和获取商业利润。第三层意义可以说女英雄形象意味着性别的社会功能角色的转换,由此赋予了影片丰富的文化政治内涵,使影片服务于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总动员。本文力图从性别与角色功能转换的角度,解读这一时期出现的众多的巾帼英雄影片,探讨它们潜在的政治隐喻与民族国家认同。
一、性别悬置中的个性消解
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这对概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一直被探讨,这对概念是既对立又互补,二者之间所构成的张力为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想象与思想的灵感。如何将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解决,在历史的英雄人物身上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在抗战时期艺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如果仅是英雄人物的浪漫崇高,这一形式贯以悲剧的来表现,比如《荆轲》《苏武》《岳飞》等题材的古装片,但在环境相对特殊的“孤岛”上海,古装历史片中的英雄则几乎偏重于对巾帼英雄的塑造。同样,巾帼英雄也是个性英雄,而在个性英雄的故事模式下,如何处理个性与国族这两种认同模式的冲突与归属问题?我们从性别的角度来考察似乎可以发现,在众多的巾帼英雄当中,可以把她们分成两类:一类是侠女型的,如红线;另一类是沙场红颜型的,如木兰与刘元度、梁红玉与韩世忠、葛嫩娘与孙克咸。
在巾帼英雄古装片热中,有一小部分影片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戏剧冲突时采用的是对个性爱情的消解方式,当然,与其说是消解爱情,不如说是对女性身份的悬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将个性意识绝对归属于国族意识当中,《红线盗盒》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她是以侠女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侠女的性别不是置换,而是颠覆与僭越。
纵观民国电影发展史,可以发现,古装片曾盛行于两个时期。第一股“古装片热”起始于1926年末,盛行于30年代初。始作俑者乃天一公司。在电影史中被称为“神怪武侠片”,这其中产生了大量的以女侠为绝对主角的影片,这类女侠身上有戏曲文化中刀马旦的影子,她们尽管是故事中武艺高强的拯救者与某种意义上的权威形象,但却未必因其善行、侠义之举最终为影片中的元社会所承认或接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文逸民导演的《红侠》③和陈铿然导演的系列片《荒江女侠》④。《红线盗盒》延续了中国电影史中女侠的形象。女侠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类型形象,她不仅是影片中的第一主角,而且是故事中的行动主体。尽管女性形象间或成为(男性)观众欲望观看的主体,但却绝少成为影片中男主人公的欲望对象,这就意味着她的形象是无性别的;在故事中,她不仅拯救陷于困境中的女性,也拯救故事里的男主人公。这一颠倒的情节模式使得侠女形象在性别扮演中充满了颠覆与僭越色彩。《红线盗盒》中的女侠红线与木兰从军有着非常相似的缘由:父亲年事老迈,但以国事为重,国家陷于危难,不愿袖手旁观,红线武艺高强,代父应征。但红线只是“代父”,并未“易装”,所以从一开始红线的性别身份便是颠覆与僭越的,节度使薛嵩并不重视,红线颇得冷朝阳的赞美也是因其作军歌草檄文,在男主人公眼里,红线是没有性别的,之后红线尽全力冒生命危险盗得锦盒,薛嵩转败为胜,也是红线为国尽忠的表现。女侠身怀绝技高男人一筹,就男主人公于危难之中同时意味着她捐弃了自己的性别身份与“人间”生活。在这里,女侠红线象征的是一份外在的、全能的救赎力量。
古装历史片不是历史,它反映的不是历史中的事情,而是现代人的观念,因为历史故事或民间故事一旦出现在艺术话语中,就变成同时代意识形态的隐喻或象征。⑤戴锦华曾指出,女侠作为电影第一主角的特点叙事,常常出现在社会急剧动荡且没有出路、没有现实解决方案的时代,它鲜有例外地成为社会的无奈与无助感的表达和想象性转移方式。⑥半沦陷时期的上海“孤岛”恰恰是处于这种无力与无助的境地:为了避免驻扎在租界周围的日本军队的干扰,也为了保持租界的暂时安定,上海市政府下令禁止公开谈论政治暴力和日本入侵。而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城中充满了各种恐怖、暗杀活动,这类恐怖活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为日伪傀儡政府。他们各自派出特务谋杀对方,记者、商人、政客等只要被怀疑或是通敌或是抗日,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杀了。在这种恐怖时局下,上海的犯罪率飙升,战时物资奇缺,人口过剩,致使物价飞涨。而此时的上海和内地大后方音讯隔绝,上海市民中处处弥漫着悔恨而绝望的情绪。《红线盗盒》中的红线,恰恰是作为一位外来的拯救者,无疑可以成就一份现实困境的想象性解决,(在影片当中,红线正是在节度使处于危难之中出现并逐步帮其击退敌兵)女性因此而被书写为社会的“他者”。这个“他者”的身份的性别毫无疑问是悬置或者说无性别的,英雄的女侠只是一个救赎与拯救的观念符号,很难说有什么个性意识。在巾帼英雄的性别被悬置的处理方式中,女性是无性的,超越阶级,超越个性意识,绝对地忠实于国族意识。
二、性别置换中的国家认同
在众多古装历史影片中,与侠女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沙场红颜的女性形象。如《木兰从军》中的木兰,《葛嫩娘》中的葛嫩娘,《梁红玉》中的梁红玉等。这一类女英雄不是性别悬置的侠女,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女性身份,尽管她们会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之下掩饰自己的性别特征,比如木兰易装从军,但梁红玉与葛嫩娘则是以眷属的身份参与到战争中来。《木兰从军》《葛嫩娘》《梁红玉》的剧情依然包含着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归属观念。木兰在军营中时刻义正词严,力求达到性别的误认,剧情发展到最高潮时是军营中月下对歌的浪漫一幕,刘元度一度认为这个与之对歌的将军就是女性时,木兰立即用军中的身份保持了自己“男性”身份,尽管木兰也钟情于刘元度,当是在“国难当头,大敌入侵”之时,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此刻,女性的个性意识再度被消解,要绝对地归属到国族意识中去。当然,与“侠女”所不同的是,性别是置换,而不是悬置,所以在这一冲突中非常关键的是女英雄女性身份的保留,这成了她们在故事中与男主人公发生爱情并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可能。当然,这种可能也只能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民族国家消除危亡之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中国作为政治的共同体至少有两种认同模式。一种是所谓的文化主义的,皇朝或国家意味着共同体的伦理秩序、道德尺度、语言与风俗等。另一种认同模式则建立在儒家正统观念的“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在晚清及至近现代中国,面对强大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国人遭受到的血淋淋的屈辱对待和利益损失使这种观念的延续有了一种自觉的国家民族主义味道,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⑦
“孤岛”上海电影中出现如此多的巾帼英雄古装影片,无不是一种家国观念在文学艺术上的折射。因此,在处理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归属的问题上,在国难当头的非常年代,个性意识是要绝对地服从于国族意识并承担起时代的隐喻或象征。古装电影叙事中个人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化解,当然,化解的方式不是解除,而是通过性别置换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巧妙的方式则表现为战争与非战争时性别身份的改换。当木兰替父从军之时,她的身份是接替父亲的角色,葛嫩娘激励孙克咸,孙终于醒悟决定加入到福建军旅中时,葛嫩娘也去掉脂粉(改成男装)随他一同参军。当遭遇爱情之时,女英雄则可以恢复女儿身,以女性的身份收获爱情,木兰最终辞别皇帝的犒赏,返乡后恢复女儿身,展现少女羞花之貌的动人姿态,重新出现在恋人面前,获得了与刘元度的爱情。葛嫩娘易装之前,乃秦淮名妓,深得名士孙克咸宠爱。梁红玉也曾一度流入青楼,与韩世忠一见钟情。女主人公通过性别的置换,一方面可以通过性别的“误识”“误辩”激发起观众窥视的欲望,但更重要的是隐藏性别身份,绝对地归属于国家,服务于抗战民族国家总动员。
三、结 语
通过性别置换的方式隐藏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直接指向的是个人要绝对归属于国家,明显地凸显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政治隐喻。而性别悬置的方式亦是对个性意识的直接消解,之所以如此,正如左翼批评家阿英所评:“在民族危亡之际,所有的人都必须团结起来,奋战救国,这是男人和妇女都应该做的。”⑧“孤岛”上海古装电影中出现的特有的女性英雄的表达方式,并非是女性主体的呈现,女英雄的形象所指涉的是忠于“君”,忠于“国家”进而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使影片服务于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动员。
注释:
① 慈祥:《论抗战时期“孤岛”电影中的妓女形象》,《理论界》,2009年第7期。
② 指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电影中频频出现的歌女、舞女以及乡下底层受压迫的女性形象自抗战以后转为对女英雄形象的塑造。
③ 《红侠》,1929年上映,文逸民导演,文逸民、范雪朋主演。
④ 《荒江女侠》,1930年上映,顾明道编剧,陈铿然导演,徐琴芳、贺志刚主演,友联影片公司出品。
⑤ 周云龙编选:《天地大舞台:周宁戏剧研究文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 戴锦华:《性别中国》,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
⑦ 关凯:《政治族群》,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 阿英:《关于木兰从军》,《文献》,1939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刘丽芸(1979— ),女,江西南康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戏剧影视学2012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电影电视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