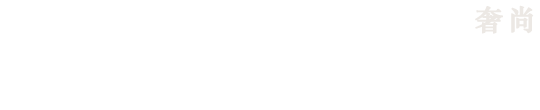姚汝勇+杨玉霞
[摘 要] “苏联电影”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体现在富有开创性的理论建设中,而且体现在高质量的创作实践中。然而,辉煌的背后却潜隐着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忧患。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个辉煌期”与“唯命是从”相互纠结缠绕,形成了当时特有的电影情势,而这种情势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它天然地因袭着先前苏联电影的气质,同时也自然地为以后电影的发展埋下伏笔。
[关键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唯命是从;教化工具论;审查制度;市场规则
19世纪曾经文学大师辈出的俄罗斯民族,20世纪又最早感受到了人类新世纪的辉煌。世纪初叶,当电影艺术蹒跚学步,还未挣脱商业枷锁的时候,列宁就对电影工作做了一系列指示,明确指出,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20年代的前苏联电影大师辈出、名作纷呈,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创造了苏联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三四十年代,在“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提出,它在丰富和发展俄罗斯学派的基本风格样式和主要表现手段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前期政治、经济上的“回暖”也为电影整个体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环境保证。然而,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的“苏联电影”在后期又遭遇了战争毁灭性的破坏,整个体系陷入一片困顿之中。
一、短暂的辉煌
三四十年代的“苏联电影”可以以194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31年至1941年。这十年中,由于国内政治(消灭富农)、经济(合作化)体制的深刻变革,两个五年计划的相继实行,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电影事业也蓬勃向前。1934年的时候,全苏联的电影院(含流动)增至29 200多家,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更为重要的是,影片题材范围不断拓展,反映苏联人民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不断增多,革命历史片与古典名著的改编也相继问世。“正是在这些年代,在社会主义从各个战线展开全面进攻的条件下,电影也像其他各种苏联艺术一样,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获得了一系列巨大的胜利。”[1]279在充满激情与宽松的情势下,电影工作者不仅迅速掌握了随着声音而来的那些电影表现手段,而且摄制了第一批重要的有声片,如《生路》《迎展计划》《大雷雨》,以至苏联电影艺术的杰作《夏伯阳》。
瓦西里耶夫兄弟的《夏伯阳》于1934年与观众见面。它是苏联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影片节奏完美,用近乎好莱坞的性格刻画手法,生动地表现了幽默、英雄精神和感情。影片以史诗般的气魂,着力塑造了红军高级指挥员夏伯阳的光辉形象。然而,瓦西里耶夫兄弟并没有单纯地赋予英雄以超人的品质,而是让“观众相信英雄人物的真实性,相信银幕上的形象,热爱他,想要摹仿他……”[1]459夏伯阳不仅是一代人民军事领袖的形象概括,而且是一位极富个性的有血有肉的普通军人。影片把个人命运同人民命运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英雄人物形象。它一度成为苏联电影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颂与塑造现代英雄人物的范例。“继《夏伯阳》之后,出现了数十部按照这一方法创作的新的优秀影片。”[2]4而且,这种创作原则也被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人所借鉴、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马克辛三部曲》(1937~1939年)、《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1936年)、《波罗地海代表》(1936年)、《列宁在十月》(1937年)、《伟大的公民》(1939年)等一批努力创造各种历史性或非历史性的“英雄人物”的影片也相继推出。一个个与西方电影人物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人物形象闪耀在银幕上,成为苏联电影学派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此外,将文学名著搬上银幕也是该时期苏联电影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影片均为世界观众所熟知。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与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也先后被摄制成影片。尽管改编的影片中尚有一些不足,但这一时期创作者的努力,不仅为文学名著的改编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确立了电影文学的应有地位。
第二个阶段:1941年至1950年。1941年夏,社会主义力量与法西斯势力之间在广阔的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殊死斗争。“法西斯匪帮燃起的战火,给苏联人民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处境,必须英勇地动员起一切力量,必须使整个国家生活适应于战时的需要。苏联变成了一座军营。”[2]581侵略战争的破坏及国内个人迷信等因素的干扰,使电影创作濒临停产。除了战时之需的“新闻电影”迅速发展外,①其他片种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尽管如此,以《攻克柏林》《青年近卫军》《玛特洛索夫》《她在保卫祖国》等为代表的影片,着重歌颂战斗英雄,强调胜利的来之不易,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不失为优秀之作。
二、唯命是从的隐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电影”创造出让人激动不已的辉煌,然而其所潜藏的问题却也十分严重。而且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电影业的顺利发展。
(一)唯命是从的教化工具论
1919年,苏联电影工业实行了国有化,在高涨的政治期望鼓动下,当局对电影已经创造的辉煌并不满意,想制造一种既能教化群众、又能鼓舞群众的电影。其实,对艺术功能的这种“宗教式”理解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间由来已久,现在布尔什维克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为之加上了权力之阀。20世纪30、40年代,苏联国家最高领导的权力更加集中,而领导干部实际上也实行终身制。政治上的权力无限膨胀,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伤及”其他方面的建设。在文化上,“各种文化单位均由国家包下来。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3]电影同其他艺术一样,毫无疑问地被置于国家和党的控制之下,并且彻底地唯命是从。政治便是艺术,政治指示便是艺术发展的方向。创作者和艺术家们成了为政治服务的符号,他们难以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难以创造性地创新。一时间,电影银幕上闪烁的似乎只剩下了被图解了的政治。就这样,电影与政治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而这种情形在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长时间里一直存在。
体制上的畸形,一方面大大地挫伤了广大创作者探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造成电影题材狭窄、公式化、概念化,脱离生活真实等种种弊端。而在另一方面,造成的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公开性”时期以及苏解体后,广大的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彻底放弃。现在,人们对政治已经厌倦了,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俄罗斯电影中的主流电影已销声匿迹,大众电影与精英电影各领风骚。显然,现在的电影一改从前板着面孔教训人的姿态,也不再充当图解国家政策的宣传工具,它终于从“工具论”中解脱出来,无疑,这是对艺术发展规律的尊重。然而,“主流电影”的消亡是不是一种损失呢?东杜列依哀叹不已。他认为,当今俄罗斯电影“作为施加社会影响的工具”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国家正在进行现代化和改革,但却没有一部影片为改革“投赞成票”。当然,俄罗斯电影现在正处于转型之中,武断地说某种方面的电影彻底消亡,可能会失之偏颇。然而,长期以来苏联当局对电影“教化”功能的固守,确实让许多创作者感到不舒服,甚至大伤脑筋。因此,90年代及其后的俄罗斯电影在困顿中探寻出路时似乎总是缺少一股“主导”的力量,便不足为怪。当然,不管将来俄罗斯选择欧洲的国家资助电影的模式,还是选择美国好莱坞的流水线商品电影,相信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会重新回到银幕上来,而那时它将是一种成熟、完善的话语形态。
(二)唯命是从的审查制度
三四十年代,苏联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步极端化,而电影的审查制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先是一定程度上允许多种声音共存的“多元论”,然后便渐渐滑入一个声音独唱的“白色恐慌”。“一个声音”,即政治的声音。而影片的审查,就是政治的评判。后来,“斯大林充当了最高审查者和全权制片人,享有决定一切的拍板权”[4]。于是,影片的审查制度便成了个人意志自由发挥的工具。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愚昧的行为,它不仅扼杀了创作者的激情,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规律,而更为严重的是把整个俄罗斯电影推向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政治审查制度愈加强硬的状况下,一系列毫不掩饰娱乐目的、甚至是涉猎“禁区”的影片却在政治上得到了审查部门的认可。G·亚历山大洛夫的一系列歌舞喜剧片和歌舞情节片,就是当时的标志。比如,《快乐的人们》(1934年)、《大马戏团》(1936)、《伏尔加,伏尔加》(1938年)和《光辉之路》等。于是,在苏联电影发展的历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当局严格控制艺术,甚至某种程度上“扼杀”艺术,但电影工作者却在困难的挣扎中时不时拍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影片。就像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怪诞喜剧片和歌舞片一样,这些作品以其帅气的男主人公和美丽的女主人公、视觉噱头和棍棒喜剧以及容易上口哼唱的歌曲来诱引人们逃避现实。不过,我必须清醒:这种类比要适可而止。因为当时苏联的状况是残酷的,正处于大恐怖时期——强迫集体化刚刚结束,千百万的人或者被处决,或者被关进集中营,或者被流放。在这种情势下,电影工作者只好“唯命是从”地把恐怖活动和美好的表象结合起,从而构造出一个虚假的美好现实。但这是不是斯大林利用电影制造梦幻的特性来缓解现实的紧张、化解矛盾而采取的“策略”呢,就像美国的罗斯福为配合“新政”而同样借助电影一样?事实似乎如此。1949年,伊凡·培利耶夫推出《幸福的生活》,这部歌舞片描写了集体农庄富足快乐的生活。从农民观众的反应来看,他们很喜欢影片中理想化的描绘。或许,“理想化”唤起了人们对生活的信心。不难理解,电影“粉饰现实”的作用帮了斯大林的忙。
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苏联电影这种独特的“救赎”功能依然被许多人所认可。为了俄罗斯经济与电影的复苏,人们纷纷“献计献策”:电影博物馆长、电影史家纳乌姆·克莱依曼呼吁向他所谓的“民族电影业对危急状况的健康反应”学习,即仿效大萧条时期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比如,弗兰克·卡普拉、约翰·福特和茂文·李洛埃的社会批判性影片,喜剧片和歌舞片(它们能提示人们,生活里还是可能有许多乐趣的,难关是可以度过的)以及历史片(它们描述过去,但并不一定总是清算过去),等等。对于好莱坞模式,坚决维护国产电影的米哈尔科夫导演认为,“美国正是靠了电影才走出危机的,”电影创造了一个人们可以认同的、使人们奋力前进的民族神话。苏联电影也有过类似的作用,他说:“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过去的意识形态,但我们确实创造了一个苏维埃人的形象并以之作为榜样。”[5]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影片中多一些光明,少一些黑暗,创作更美好的电影(“舒心的”电影)。而处于困顿现实中的俄罗斯也似乎从不缺乏这样的实践。比如1993年德·阿斯特拉罕导演的《我只有你一个》,片中一支70年代的歌充溢着积极的思想内涵:“贫穷的、亲爱的祖国,我只有你一个。”穆拉托娃1994年拍摄的《迷恋》,银幕上的一切都很美,人与自然和谐融洽……而米哈尔科夫潜心打造的《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则“试图给俄国人民制造出一个理想的俄罗斯:一个美好的世界,有高尚的道德、纯真的爱情……”所有的忠告听起来都有道理,创作者的实践也颇让人欣慰。但如此种种于艰难复杂的转型中的俄罗斯电影到底是不是一针有效的“强心剂”呢?彼·托多罗夫斯基说,我不认为某一部影片可以改变现状或者使人民的状况变好,但是坚信一点——“(我)不拍阴暗消极的影片”[6]。唯此而已吗?有趣的现象挽救不了畸形的审查体制,戈尔巴乔夫时期,它便遭到空前的攻击而消亡。
(三)唯命是从的“市场”
资产阶级的生存法则是:让市场决定一切。这在苏联从来没有被采纳过,更不用说从30年代开始的斯大林时期。党指挥一切,党包办一切,市场是没有市场的。苏联的国产电影从制片到发行放映,完全处于“井然有序”的计划体制之中,不愁断了“香火”。而国外影片的绝对限额甚至完全不准进口公映,更使国产影片“自给自足”,养尊处优。虽然国家对电影的这种买断式的“包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国的电影院,包括最偏远地区的电影院的工作畅通无阻;保证了电影在俄罗斯广大城市和有偿服务;保证了国产影片在上映片目中的主导地位,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本土电影脱离了与外国电影竞争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竞争力。其次,生产只管生产,不管发行,影片能否上映,受不受观众欢迎,似乎与己无关。反过来,发行单位也没选择影片的权利,给什么就得要什么,即便没人看,也得照样购买。这样,不仅调动不了创作人员及发行放映人员的积极性,也极大地影响了电影整体质量的提高。所以,“公开性”及苏解体后的长时间里,俄罗斯国产电影面对蜂拥而入的国外影片,特别是美国电影,显得束手无策——它的电影市场迅速被好莱坞的爱情、性、暴力、战争等占领。而本土电影在怒气冲冲地和旧体制“对着干”的欢愉中,在手忙脚乱的拙劣仿造中,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而更为惨痛的是俄罗斯电影整体水平飞速下滑,观众大量流失。长期以来,市场的缺失、行政命令式的“国家定货”,使国产电影整体上羸弱无力。而俄罗斯国家电影委员会副主席C·拉扎鲁克在1997年的一个报告中这样说:“苏联电影可能缺少创作自由,但从不缺少观众的注意。”我们不能否认苏联电影的巨大“魅力”,更不能掩盖热爱艺术的俄罗斯人民对本土电影的钟爱。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体制上长期以来形成的痼疾,给人民选择的机会并不太多,而且实实在在地对现在的电影业造成了深深的创伤。所以,C·拉扎鲁克的说法,我们权且把它算作是俄罗斯电影人聊以慰藉的话吧。
1941年5月以后,斯大林集党的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于一身,独掌党政军大权。这种情形在反法西斯战争等特殊时期是必要的,但在战后仍然延续,难免会造成恶劣的后果。苏联电影从4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入停滞、衰退阶段,1951年达到最低点,年产影片仅6部。“苏联电影”到底还是被褊狭和妄想狂折腾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三、结 语
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从此,在俄罗斯土地上飘扬了74年红旗易为三色旗,苏联解体。而“苏联电影”以及它的贡献也在那一刻成为历史的陈迹。目前,“苏联语境”已然消失,它特有的矛盾气质——沉重的负载下面闪烁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在自由狂放的新生态中,也已不复存在。进入21世纪,俄罗斯电影仍在努力“转型”。现在,它既不是一个梦工厂,也不是一个娱乐王国。因而,对苏联电影的成败得失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发现历史的教训,或许会对从俄罗斯到乌兹别克的各民族的“苏联后电影”的勃兴提供一个有益的历史参考。
注释:
① 整个战争期间,共发行《苏联电影杂志》400号,《每日新闻》65号,《战地电影专辑》24号,67部标题短片和34部大型纪录片。当时拍摄的350万米胶片,现在已经成为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伟大卫国战争电影编年史。
[参考文献]
[1] 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苏联电影史纲(第一卷)[M].龚逸霄,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2] 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苏联电影史纲(第二卷)[M].龚逸霄,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3] 孔祥云,刘敬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2.
[4] L·梅纳什.苏联电影(1917-1991)的历史经验[J].桑重,译.世界电影,1995(06).
[5] L·梅纳什.莫斯科还是相信眼泪的:转型期俄国电影的问题(与希望?)[J].章杉,译.世界电影,2002(01).
[6] B·托多罗夫斯基,等.俄罗斯电影人的忧虑与期盼[J].胡榕,编译.世界电影,2001(04).
[作者简介] 姚汝勇(1974— ),男,山东德州人,硕士,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理论与批评。杨玉霞(1977— ),女,山东潍坊人,硕士,聊城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