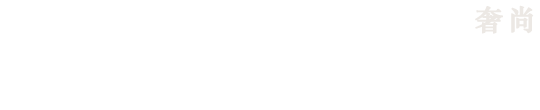[摘 要] 作为隐藏在人类潜意识中的一种强大力量,欲望往往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在影片《白鹿原》中,众多人物自身膨胀的欲望充分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影片《白鹿原》从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其影视叙事的文化意义,即以“物欲”为主题的文化意义,集中体现为对土地和金钱的欲求;以“权欲”为主题的文化意义,集中体现为隐性权欲者、权欲牺牲品和权欲反抗者;以“情欲”为主题的文化意义,集中体现为由情欲促成的爱情、夹杂着温情的情欲和由情欲滑向色情。
[关键词] 《白鹿原》;影视叙事;文化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资助成果(项目编号:12JK0387);2013年度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课题成果(项目编号:13L85);2011年度西安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1QDJ029)。
欲望是一种隐藏在人类潜意识中的强大力量,它常常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危机。因此,对于欲望的表现程度,就成为衡量文学或电影挖掘人性深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影片《白鹿原》以“欲望”为主题,向人性的纵深处开掘,通过影视叙事展现了丰富的文化意义。
一、以“物欲”为主题的文化意义
物欲是隐藏在人性中的一大本能欲望,通常被理解为是对物质畸形而无限制的欲求。在影片《白鹿原》中,物欲集中体现为对土地和金钱的欲求。
(一)土地:物欲的深层表征
在影片《白鹿原》中,土地是被反复强调的一个物质符号。土地是一种能够生长出庄稼、能够产出“物”的资本,因此是物欲的一个深层表征。影片中反复出现金黄色麦地的镜头,一方面,暗示了人们对于“吃”这一正常物质的合理性诉求;另一方面,促使“物”的意义获得了足够的增殖空间,使影片中“物欲”的语义殖得到了强化。此外,对于这些以土地为生的麦客们世俗的日常生活,诸如割麦、吃饭、睡觉、吼秦腔等关涉到物质的元素,影片对之进行了着重而重复叙事的处理,使得物欲得以突现出来。
(二)金钱:物欲的间接表征
金钱与物欲之间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为金钱能够换取物质,进而实现对物质的欲求。可以说,金钱是物欲的间接表征。最初与黑娃的牵扯,使得田小娥远离了富足的物质生活。黑娃出事之后,田小娥面临着生存危机和困境,甚至正常的物质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影片中的田小娥从鹿子霖、白孝文那儿获得了不少金钱,其数量似乎仅仅能够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这并不能够否认其对物欲的放弃,尤其是白孝文拿着卖房产所获得的最后一点儿钱带着田小娥去城里吃、喝、玩、乐的一番表现足以证明这一点。影片用铺陈的叙事手法表现了二人奢侈的物质享乐过程,显然,导演对其追求世俗物质享乐的行为是报以道德批判意味的。当然,“人对物的毫不抵触的拥抱事实上是人的一种自我放弃”[1]。白孝文和田小娥的这种对物质狂热的世俗享乐是其自身物欲膨胀的最后挣扎,但与此同时,也是他们的一种自我放弃,是走向生命尽头的回光返照,很快二人就因饥饿而濒临死亡。而当白孝文不知廉耻地拥挤在乞讨人群中甚至处在苦于无碗盛热粥的窘境中,影片对其物欲的道德批判在物质匮乏所导致的生存危机面前消失殆尽,这是因为,正是出于物质匮乏的现状,才对物质充满了无穷的占有欲望。
二、以“权欲”为主题的文化意义
权欲,通常意味着在外界社会层面上,通过实现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以期获得声望、名声等内心的精神满足,往往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对于权力的欲望、牺牲以及反抗,在电影《白鹿原》中似乎从未停止。
(一)白嘉轩:隐性权欲者
传统社会的权力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维系和掌控纽带的,因而具有更强的封闭性和承袭性。在白鹿原上,“族长”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具有极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因此,白嘉轩在众多人物当中的权欲可谓首屈一指,然而,其权欲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即在实施和贯彻“乡约族规”的掩盖下得以实现。白嘉轩以其“族长”的身份、以乡约族规的名义实施了许多措施,其中不乏一些仁义之举,如兴办学堂,支持黑娃上学,大灾时施舍义粥;此外,也包括一些饱含封建宗法色彩的举措,如拒绝黑娃和田小娥入祠堂拜祖宗,惩罚黑娃和田小娥,惩罚白孝文和田小娥。“对权力的病态追求所包含的支配他人倾向,并不一定公开地表现为一种针对他人的敌意。”[2]表面上看,这些行为是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依照乡约族规承担起的族长责任,看似是一件件大快人心、顺应民意的事情,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也是白嘉轩权欲倾向的显露,是支配他人、满足自我权欲的结果。
(二)白孝文:权欲牺牲品
作为未来接替老族长白嘉轩的继承人,白孝文的整个成长过程都严格遵循未来族长的标准,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是白鹿原上的“第二个”白嘉轩。一方面,其父的权欲在其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强化;另一方面,以族长标准接受培养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权欲无限膨胀的过程。随着白嘉轩的逐渐老去,白孝文渐渐承担起了许多族长的职责,忠实地执行乡约族规,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人们自以为在做什么,而实际上却只是在为另一种东西服务的工具”[3]。白孝文在看似实现其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实际上却成为实现自身权欲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是彻头彻尾的权欲牺牲品。从这个层面上讲,白孝文既是自身权欲的牺牲品,也是“族长”这一权力符号的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小说中已有两个孩子的白孝文,电影却安排了他膝下无子,“性无能”情节的处理充分揭示了白孝文在长期外力强迫性的理性塑造之下被抽空了其正常而丰富的人性诉求,在社会性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却丧失了作为人更为基础和本能的自然性。因此,影片对于白孝文在长期的精神压抑之下导致的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生理问题的处理,深化了白孝文这一人物的悲剧色彩,强化了权欲对于人性的异化和迫害。
(三)田小娥、黑娃:权欲反抗者
作为“族长”强大权欲的反抗者,田小娥始终是被排斥在由权力所设置的秩序之外。后来,不管是为了救黑娃委身于鹿子霖,还是为了报复白嘉轩诱惑白孝文,抑或是处于对白孝文的同情而以弱者柔弱的方式报复鹿子霖(向鹿子霖脸上撒尿),始终是作为“物”被排斥在男权社会的权力之外,甚至是在权欲的支配下成为男权社会中任人宰割的羔羊。当然,田小娥并非一味地顺从,而是在自己弱势的境况之下,以女性天然的身体作为武器,反抗和报复强大的权力体系及其最高权力代表(族长)。而另一个权欲反抗者——黑娃,从小就受到权欲的支配而选择主动逃离和自我放逐。显然,其被权欲支配的身份(长工的儿子)以及受权力的威慑(白嘉轩挺直的腰杆)在其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和反抗的种子。后来,黑娃以土匪的身份亲手打折了权力的象征——白嘉轩的腰杆,试图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对权欲的反抗,当然,其对权欲的反抗本身却体现了其自身权欲的膨胀。
三、以“情欲”为主题的文化意义
影片以“情欲”作为关涉的结点,把田小娥与几个男人的关系作为了叙事的重点,[4]主要涉及人物有黑娃、鹿子霖、白孝文。
(一)黑娃:由情欲促成的爱情
白鹿原是一块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盛行的地方,因此,人们对于婚姻的定义,当然取自封建传统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个人而言,则是尽力克制和掩饰个体的冲动,极少有机会在“情”的基础上建立起婚姻家庭关系。然而,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却是始于爱慕,源于情欲,终于爱情。因为,只有像黑娃这种从小较少受到封建传统文化浸染的人,才有可能实现由情欲最终走向爱情的道路。黑娃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即使是在东家白嘉轩的极力支持和劝导之下,他仍然坚定地拒绝接受封建传统教育。对于黑娃与田小娥得以结合的这一重要且根本性的原因,影片不仅没有像原著那样进行较为细致的交代,反而做了全然忽视的处理,这不得不说是影视改编的一大缺憾。“当人们爱的时候,他想获得什么东西,他也想付出什么东西,这双重目的使爱情变得比吃饭睡觉复杂。它既是自私的而同时又是利他的。”[5]表面上看,影片并没有触及所谓的“爱情”以及其中复杂的人性,而仅仅实现了情欲上的满足和召唤,但显然,影片对于黑娃和田小娥之间的情感处理还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些许温暖的爱情。
(二)鹿子霖:夹杂着温情的情欲
情欲是对他者的冷漠,具体表现在“唯我”中心对他者的征服、支配上,即通过情欲打击、控制、征服他人。不仅与田小娥、且与白鹿原上许多妇女有染的鹿子霖,在情欲的放纵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唯我”的世界,即以自我为中心、从自身出发满足情欲,在这一过程中,鹿子霖不仅从他人身体中体验到了自我肉身的存在,同时,是对自我特权和对应于受者的施者身份的确认,在对他者的征服、支配上实现了男权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在田小娥受惩受伤之后,鹿子霖为其疗伤、治病,似乎显露出在情欲的背后还存在着些许令人欣慰的温情,然而,“由于‘爱抚,情欲可能蒙上一层温柔的爱情面纱,但是,情欲核心的‘唯我性又残酷地揭开了爱情织成的遮羞布”。[6]鹿子霖这种在温情掩盖下的情欲最终仍无法掩饰其情欲的实质。“为了防范他人的自由并把他人的自由作为自由而超越,自由和他人就崩溃了。”[7]在以情欲征服、支配他者的过程中,鹿子霖通过情欲施者的身份,实现了对受者田小娥的征服、控制和打击,以便在情欲的过程中确证自身“唯我”的地位和特权,从而排斥他者及其他者的主动性和自由性。值得强调的是,鹿子霖对田小娥的情欲征服,是基于对他者的冷漠,并没有放逐、冷漠自我。
(三)白孝文:由情欲滑向色情
白孝文最初受田小娥的诱惑是基于其情欲的诉求,因为作为未来的族长,他当然有类似于鹿子霖“唯我”的特权意识,由这一意识引发的征服和支配他人的欲望转嫁为对田小娥的情欲诉求。一方面,情欲以身体的接触实现双重的肉身化,另一方面,施者自我同受者一起被情欲拖入了一个混沌的世界之中,放弃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这样做的结果必然由情欲滑向色情。色情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崩溃,不仅对他者冷漠,也对自我冷漠。当事情败露、二人公开在祠堂受罚之后,白孝文随之丧失了“族长”的身份和地位,也即丧失了“唯我”的特权意识,从而在对自我肉体的彻底物化、他者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自我的彻底冷漠和放逐。这个时候,自我与他者一样,成为物质交换的双方,具有鲜明的交换性。由此,身体作为一个符号的载体按照等价原则从事交换,“形式上的公正经常伴随着一种冷酷无情”[8]。交换得以实现的基础是白孝文不仅把作为他者的田小娥符号化了,而且也将自我符号化了;不仅出于对他者的冷漠,也基于对自我的冷漠,至此,白孝文完成了对田小娥的由情欲滑向色情的过程。
当然,电影《白鹿原》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缺憾,诸如对于黑娃这一重要人物形象的成长、发展、转变等一系列人生轨迹的交代显得残缺不全,又如影片明显缺少百灵、鹿兆鹏这条线索,然而,就透过人物潜意识中的“欲望”、挖掘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这一点来看,应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
[参考文献]
[1]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M].上海:三联书店,2002:264.
[2] 卡伦·霍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43.
[3]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3.
[4] 徐汉晖.论电影《白鹿原》的艺术缺失[J].电影文学,2013(03).
[5] 佛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40.
[6] 陈林侠.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4.
[7] 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493.
[8] 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83.
[作者简介] 郭萌(1979— ),女,陕西榆林人,博士,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